腊月二十八立春。正月十五刚过,一场早春雪就在人们还浸着年味的梦里悄然覆盖大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不要说蕾的娇媚、花的浪漫、果的深沉,在四季之中、流云之上、天地之间,或舒缓飘逸、或飞扬灵动、或含蓄滋润的雪,令人想起来意味难穷、望过去荡气回肠。含蓄滋润的,便是早春的雪了。
有“儒书”底子的父亲,在“七级工八级工不如三沟萝卜两沟葱”的年代也丝毫没有弃工回乡的念头。干煤矿的三十年里有二十八年在井下,一辈子就这么平铺直叙地活着、不声不响地做着,然后如早春的雪一般悄然而去。
 三十三年前,就是父亲刚刚退休回到山村那年的一个上午,下了场挺大的春雪。虽然山坡上的杏树已经开了花,在“窨子”躺了一个冬天的地瓜也被人们弄醒,一排排安放进育苗的畦子里,但那时的春寒远比如今这个早春料峭许多。所以,父亲望着结实实、沉甸甸的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春雨贵如油,春雪美似酒”。又俯身从墙旮旯摸出个酒瓶子,说:“把开春后下的雪装进瓶子里,埋进地底下,等进了‘伏里天’就起出来,用雪水给娃娃抹痱子,蛮灵。父亲这么说着、做着的时候,抬眼我望见春雪覆盖的山坡,白里透红的好看。退休后的父亲在山村蜗居了二十三年,十年前因“矽肺”癌变去逝。正值早春二月,稀疏的雪花无精打采地飘着,父亲躺在我睫毛上水晶一样的泪里,光彩夺目、万般慈祥。那一刻,记起关于父亲的许多事,以及父亲把春雪装进瓶子里的那个上午,儿子对父亲的那种留恋,未上眉头,却上心头。
三十三年前,就是父亲刚刚退休回到山村那年的一个上午,下了场挺大的春雪。虽然山坡上的杏树已经开了花,在“窨子”躺了一个冬天的地瓜也被人们弄醒,一排排安放进育苗的畦子里,但那时的春寒远比如今这个早春料峭许多。所以,父亲望着结实实、沉甸甸的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春雨贵如油,春雪美似酒”。又俯身从墙旮旯摸出个酒瓶子,说:“把开春后下的雪装进瓶子里,埋进地底下,等进了‘伏里天’就起出来,用雪水给娃娃抹痱子,蛮灵。父亲这么说着、做着的时候,抬眼我望见春雪覆盖的山坡,白里透红的好看。退休后的父亲在山村蜗居了二十三年,十年前因“矽肺”癌变去逝。正值早春二月,稀疏的雪花无精打采地飘着,父亲躺在我睫毛上水晶一样的泪里,光彩夺目、万般慈祥。那一刻,记起关于父亲的许多事,以及父亲把春雪装进瓶子里的那个上午,儿子对父亲的那种留恋,未上眉头,却上心头。
父亲去世五年后的早春,正月十三的晚上,我走在西山公园里。一株株、一排排、一片片的杨柳树、法桐树、松柏树矗立得安静。树影印在路面上,我缓步在树影里。沿路,杨树的影子像棕榈、法桐的影子若梅花;明月松间照,撒下光辉点点,呈千万个月亮。还有残雪偎在石墙,怀念远去的云彩,做着春天的轻梦。当此时,出了公园,怕这好的月光就灭了,便停下来。我在努力地想像,但我觉不出,满园月光哪一片“奶油一样能用小铲子铲起来”,它始终只是月光。我在刻意地寻找,但我不知道哪一缕月光“曾经照古人”、曾经打量过父亲在人世间的七十七个春秋以及父亲三十年往返于煤矿和山村那十多里的黄土路。确凿的事实是,除了一些月光,还有许多雪、春雪、早春的雪落在父亲就像他身板一样瘦瘦的一辈子里,从生到死。
八十五岁的母亲眼晴基本失明,一大早就摸索着起了床。待我起来推窗望见白茫茫的一片,告诉母亲说“下雪了”。母亲愣了一下:“哦,下雪了”,又说“快到你爹的忌日了”。是的,快到爹的忌日了。那天,我或许会带上把装了雪水的瓶子到父亲坟上去,毕竟父亲说过:“春雪如酒”。
春雪如酒 | 怀念远去的云彩 做着春天的轻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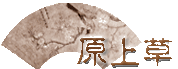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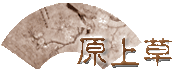
如同攥起的流沙,
还未来得及看清它的形状,
就从指缝间悄无声息的滑落了,
只留下青丝掺杂白发惆怅在你的发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