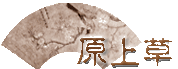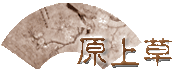较之于“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的苔米,原野上的草们该是更富说头了。纵使大唐那位白氏,以“赋得体”写下“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精品绝唱,许久以来,心胸里总揣着想就这草们说些什么的冲动。要说的这草们,是故乡的原上草。
故乡村庄的四野,其宽阔度以东南为最。有山,并无怪石也无参天乔木,梅雨季常见浮云盖顶,朗晴天或有青烟横腰。有坡,青石板枕卧,荆棘择处丛生,石砌的牛圈、“石屋”渐次淡出岁月的云烟。有沟,正南直走去北,转而向西,接城镇则尽,像山根的末尾开出一朵花。无论这山、这坡、这沟,各色的草离离亘古,岁岁枯荣,生生不息,二百年的村庄和村人与草们相依为命。
概因人迹多至,又有牛羊踏蹄,表土肥壮有加,南山坡的草尤其丰茂。这地处的草我叫不出它的名字,只知它修长有节,一簇簇相拥着满山坡向上生长,单株上的叶子并不紧凑,抽芦花样白间点蓝的穗,待到入秋长足了身量,随了风的舞蹈回环, 前俯后仰、左右旋绕,如波似浪。满山坡的这草丛里,杂生荆棘和山韭菜,花开杏粉、高低挺立、刺满周身的“大蓟”也有。荆花盛开的时候,这草也得了幽香,它那摇晃涌动的穗往往拂过蜜蜂的翅膀。除了孩子,大人们也经不住成熟泛红的酸枣的诱惑,䠀过这密实的草丛、穿过扎手的针刺一枚枚摘取,如是抚摸远处的童年。这草丛里、荆棘中的山韭菜并不成片,一窝窝地长,薅采来即可做成美味佳肴。这草的腐叶经年陈积,遇雨即生出黝黑亮绿可食的菌类,乡人称“黑娥子”“地瓜皮”。见了那“大蓟”只是绕开了走,有的俯身打量它杏粉的花,说“这花挺好看,若非身上有刺”。生产队那些年月,看看就要忙秋,就要千斤成吨地分地瓜,便打发家里的孩子去约定成俗、“自家”的那块山坡皮“割薄板”,就是把青石板周遭的这草用镰刀割走,好亮堂堂地晒地瓜干。
前俯后仰、左右旋绕,如波似浪。满山坡的这草丛里,杂生荆棘和山韭菜,花开杏粉、高低挺立、刺满周身的“大蓟”也有。荆花盛开的时候,这草也得了幽香,它那摇晃涌动的穗往往拂过蜜蜂的翅膀。除了孩子,大人们也经不住成熟泛红的酸枣的诱惑,䠀过这密实的草丛、穿过扎手的针刺一枚枚摘取,如是抚摸远处的童年。这草丛里、荆棘中的山韭菜并不成片,一窝窝地长,薅采来即可做成美味佳肴。这草的腐叶经年陈积,遇雨即生出黝黑亮绿可食的菌类,乡人称“黑娥子”“地瓜皮”。见了那“大蓟”只是绕开了走,有的俯身打量它杏粉的花,说“这花挺好看,若非身上有刺”。生产队那些年月,看看就要忙秋,就要千斤成吨地分地瓜,便打发家里的孩子去约定成俗、“自家”的那块山坡皮“割薄板”,就是把青石板周遭的这草用镰刀割走,好亮堂堂地晒地瓜干。
顺了山的坡势下行去村庄方向是为良田,如是当年社员出工叫“上坡”,良田地段依然是坡。虽则西高东低的山村,这良田却是土层肥厚,于蛮有高度的土崖上挖一平进直入又七拐八弯的洞,即成生产队为来年留存地瓜种的“地窨子”。所以,只要不遇灾年,良田里庄稼长得好,草们也是借势疯长,即便一茬又一茬被“锄禾苗日当午”。伴生于田间里、地头上、堰跟旁、小径边的草们,族类之众,数不胜数。凡若狗尾巴草、灯笼草,“打猪草”的伙伴也是不要,可以拿狗尾巴草的穗儿扎成“老鼠”来玩,可以掐它的一穗自圆茎处扯开多半,贴于鼻孔处扮作“大鼻子”;灯笼草有结实带棱的杆,杆上顶着多支细梗挑起的碎花,将它的杆由中间往两端劈开,可弄成方形、菱形来看。有种叫“结结草”的,扁平铺地放射而生,接根处有白生生甜味的、层复的叶,技巧者能采之作哨以吹;有种“热草”也叫“不死草”,越是天气闷热越是忙不迭地长,即使连根拔起扔到路边,遇雨再生。这种草不光生命力强,还汁嫩,结细小的“乌米”,所以可一铺一捆地采来喂猪喂鸡、给饲牛羊;如若赶了嫩黄的雏鹅牧于田间野径,便猛逮了这结结草、热草而食,一会功夫那吃进去的草“鼓囊囊”显于脖颈。还有一种草,人称“㩐倒驴”,凡无湿地、水塘、溪流之处则不生或稀少零星,其叶结实劲道,驴啃食而拔,或能把这驴子就诳倒了,故名。那种大多长在生土堰上、用镢头无论如何也掏不尽的茅草,有宽且长、筋脉坚韧的叶,搓绳之用无以取代;有节状的、发达的、甜甜的根,是穷困年代孩子们的喜欢。
那条沟叫“大南沟”,源出东南山间的谷地,尤见石块砌碹的桥。直至村头约三四里的一段,两侧至高处壁立两三丈,除繁生灌木棘刺、这藤那蔓、种植的“棉槐”,秀于其上的是“黄柏草”了。其色泽褐黄,叶整、干粗、结实挺拔,若论身高,故乡的原上草无可与之比拟。“黄柏草”抗腐,其用不可以喂牛羊,能生火做饭但可惜,于是编搭成“草栅子”铺炕、防冻、防雨,有编织成“蓑衣”的,雨天披着它南山坡放牧牛羊,掀蝎子、逮蚂蚱、捉“山翅牛”。“黄柏草”的根,其用可作刷锅洗盆的炊具,只是较难掏腾,须小心踩实了高突的土崖,用镢头尽力往深处掏,这般方能把它的根系更多更长些地掏出来,然后洗净泥土,最好再以开水蒸煮,辅之一木柄,以粗细适中的铁丝绑结实,耐用的炊具就成了。
“大南沟”中段、沟底东西向接连两处山坡交点那里,有“草台子”,村里人都这么叫。实则就是一相对开阔高大的土坡。土色暗红有粘性,杂糅不规则或圆溜的碎石,不长能饲牲畜的草,有野菜却不丰盛,“黄柏草”也有但长得矮小,可能叫那粘性的土拽得少了“长劲”吧。伙伴们相约去“打猪草”:“上哪”,“上‘草台子’”,其实是因了这去处更好玩一些,因为这里没有多少可采撷的野菜。从“草台子”再往北,近村头那里有“南井”,井筒石砌由底到顶,水不丰,多由地表渗水,若冬季闹了水荒,间有村人以扁桶来汲水。有年为井底清淤泥,光棍“老赫”自告奋勇,事毕,曰:“下井容易上井难,上井时候,踩着井邦只是低头或平视,若是朝上看,直上直下地,远;井口大的天,铮亮得眼晕,悬。”是走势又低、呈发散状,象是“三角洲”的原因吧,“南井”这地处“热草”丰旺。那年秋,玉米地已是没了人头,独自去这里“打猪草”,忽闻阵阵的“呜呜”声,心里顿生惊悚,想到周遭有坟,继而头皮腮帮子发麻,于是拿石块“铛铛”敲镰刀,因为听大人们讲过,“邪魅鬼祟”怕这。“南井”又往北靠了村头,是唤作“土场”的地处,“四队”里的人长年于此取土,或“垫栏”或“揣搭货”,遂成一若大土坑。伏里天雨水多,这土坑每每灌水满满,只是并不深,上坡“打猪草”或就这近处放雏鹅的男孩子时常光顾这里,赤条条玩水冲凉;到了晚上,偶尔也有女孩子来,借了玉米的掩护再加上个放哨的,一样的赤条条扑腾。无论男孩子、女孩子还是大人们,上坡或下了坡,自田间小路经过这里的时候,往往喊上几声,因为“土场”这儿还是一处“回音壁”,那撞上土崖又弹回来的声音比原声好听呢,然后“嘿嘿呵呵哈哈”地笑,转头继续走路。
“三月茵尘四月蒿”的“白蒿”该应归于草吧,还有含了“青蒿素”、可用来做“豆豉”、可拧成绳熏蚊子的“黄蒿 ”,以及能入中药的“益母草”,也是草。至少它们有着草性,不择肥土、不惹人眼,由了天地自然而生,亦属“田间无闲草”的善本生灵。至于从山与坡的折线直达山顶那里所生长的草们,大概是没有多少说头的,它们盘居的这地处土皮薄、不肥,所以便长不高也长不好,基本不受人们的待见。它们只是坚守,用根系的驻扎和叶翼的护佑,不至让那薄的土皮儿被一场场的雨水和居高临下的山溪冲跑,话说回来这也是在固执地守护自己的命。相比之下,良田那儿的地头堰边则是孩子们“寻宝”的不二之选,搁下“打猪草”的篮筐,拨开缠来绕去、勾勾挂挂的藤蔓,往往就能瞅见车厘子、托盘儿、大酸枣。在心里头,这类诱人的“野味”,还有“天星星、酸溜溜,屎瓜儿、甜秫秸,大苦菜、小苦菜、青青菜、马榨菜”,以及听大人说可以看而不得吃的“瓜蒌、羊角瓢、娃娃拳、狗奶子”之类,统归故乡的原上草。它们是长留在野坡沟崖、田间地头的童年,是曾经的那年那月那种日子的喂养和供养,是所有记忆中更纯粹更透亮更美好的影像,挥之不去正若如影随形、刻骨铭心。
进了晚秋、冬季和早春,故乡的原上草不外有三个归处:积肥、饲畜、烧饭。
“积肥”是生产队的事,把那些绵柔易腐的草比如“热草”、树叶、秸杆的叶等等,搅之以土、注之以水,外层用泥浆抹严实了,来年便可为耕地追肥。“饲畜”这事,生产队里的饲养员须好生生办,凡见适用的草就弄将回来,积少成多喂牲畜远比那类用铡刀切碎的秸杆要好。年年冬天,东邻明成老哥家的园子里攒有两个“柴禾垛”,一个是“秫秸垛”,另一个就是“草垛”,足以管饱喂养的两头牛和一只奶羊。至于“烧饭”,起初的活儿就是家里孩子们的营生了,因为不管是“硬柴火”还是“煊柴火”,都得先从野坡地弄回来,况且孩子们没有不乐得去做这事儿。做得多一些的应该是“搂柴火”。就是扛了耙子、带了绳子,去山坡上、野地里或沟底的崖头下,约莫凡有枯草、有干枝、有烂秫秸的地方,便奔了去可劲地搂啊搂,看看已经积攒了一大堆,只是“蓬蓬”地不实牢,便以膝盖跪上如此这般地拢几拢,然后拿绳子捆个结实牢靠,用耙子挑上背回家去。算作“技术活”的是“割山草”。一般是去南山坡那里,专割还算结实“抽芦花样白间点蓝的穗” 那种草。镰刀要足够锋利,左手挽住薅过来,右手持镰刀尽量贴着山皮加力往身前一带,一把山草便割下来。如此重复着这般动作,一铺一铺的山草就落到了身后头,渐次便可捆扎成蛮大的“草个子”,“小社员”收获喜人的大成果。尤其有意思的是蹭“草根子”了。大致要在早春,这是因为贴着山皮长的这草开始抽芽,更加“厚敦”、耐烧。山坡上寻见连成片的“草根子”,轻巧地挥抬镢头,只要是蹭断了它的根,便可一片片地得手。“嗯,不少了,差不多了”,就横了镢头,把蹭好的“草根子”拢成堆,两手一掐掐地、实牢牢地摁进“架筐”里去。至于用这原上草生火烧饭,孩子们可做的营生大概只有听了母亲的吩咐,去续草烧灶这么一件了,除此常常就是母亲窝在烟熏火燎黢黑的饭屋里,烧鏊子、撑勺子、运“筢子”摊煎饼。那圆圆的、一张张的煎饼层叠着摞在“盖垫子”上,正似一摞摞的日月,于循环往复的光阴里供养着一个家。
有说“所谓故乡,不过是祖先流浪历程中的最后一站”。那么,故乡的原上草或许就是哪一年哪一天的哪一场风,或者哪一年哪一天的哪一种鸟,把这草们的种子搬运到了这里,在这里发芽扎根、繁衍生息,遍布这里的山坡、田地、沟崖,不离不弃与这里的阳光、空气和粮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十七岁离开这里的游子,常常感念着故乡的点点滴滴,感念着故乡的原上草;所以,四十三年后,有了这篇抒怀且释怀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