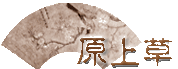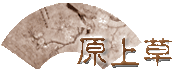村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差不多。小麦白面得算计着吃,包水饺吃水饺基本是给逝去的先人上个坟和到了过年时候的事,三餐煎饼咸菜窝窝头是常态。养群鸡攒了蛋能换点买盐称油钱,想要换来整整装装地“大钱”还是养猪。无论什么时节,无论人畜草木、耕地粮食,无色无味透明的水都是生命的源泉。如是,那日子简洁明了得只不过咸菜、泔水和水瓮这“三口瓮”。
那些大大小小、粗细深浅、样式大同小异的瓮,不外乎“瓦瓮”和“陶瓮”两种。瓦瓮的皮壳儿薄,外层没有滑溜的釉,质地也不够坚固,盛之以水易渗,所以这“三口瓮”就成了与之反比的陶瓮。
“咸菜瓮”大都放置在天井的一隅,若是放到屋里头,夏天会散发异味,不爽。为了防止雨水入瓮 —— 不然会“起白花”,也叫“生花” —— 一般会在瓮口横上几根木棍,蒙块塑料布,再压上块青石头;将就些的人家,可能拿木板子拼个瓮盖再拿塑料布裹上,就更加“板整”。淹咸菜用粗盐,可以不用上碾碾碎、推磨磨细,据说粗盐淹制的咸菜更能刺激味觉神经,让人更清晰的感觉到咸味里的鲜味。淹咸菜用的蔬菜多为“辣疙瘩”、白萝卜、胡萝卜,初时淹上大半瓮,要是瓮里的水有些“㸆”了,便再续一些、再添些盐,总要让水漫过咸菜一两拃,一来能让顶头的咸菜全身入水,二则还能随手把日常做菜弄下的“边角料”或从自留地摘来的什么菜,比如白菜根、黄瓜芭、嫩扁豆、缨帮叶、青辣椒、生豆角之类丢进这咸菜瓮里去。

我们家有前后两个院落,后院靠北,有个青石块砌口的水池,夏季的雨水由“羊沟”入池,冬季“坐了清”即是饮用水;有片长势还好的香椿树,春来长出的头茬可采了全身入盐淹成咸菜,秋天只能撸它的叶,咸菜瓮就靠了水池立于椿树下。家里是在什么年月置办了这口咸菜瓮、淹了满满当当的一瓮咸菜,我没有丁点儿印象,或者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了,只是我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就一直立在那里。许多年前的画报上,有幅获奖的照片,题名“中国人的早餐”,景物便是白雪覆盖了尖顶盖、近景至远景的一拉溜咸菜瓮。我家的早餐、我的高中两年,每一天都没离开水池旁、椿树下这口咸菜瓮的供养。一九七九年,村里同一级的初中同学升高中只考上我一个人,全班也只考上包括我在内的四个,这年我十五岁。上高中在区属的第六中学,学校在外村,从本村去学校要翻一座山、穿一道沟、过一个村、走一条沙子路。因为路远,所以住校,每周往返一次。住校的餐饭,除了偶尔从家里背些麦子换饭票能吃上馒头,平常便是母亲摊的煎饼。尤其在夏天,要是煎饼发馊“长毛”,就用学校食堂蒸馒头的“馏锅水”涮两遍再泡了吃,“就菜”便是家中那口瓮里的咸菜。每次周末回家该返校了,便用那个棕色、足够装上能吃一周的“食母生”瓶子鼓捣咸菜。“辣疙瘩”结实、口感还好,从那瓮里捞出来,洗了、切丁、装瓶,再弄个干辣椒、抓上把芝麻,铁锅里略炒,拿“蒜臼子”捣碎并倒入酱油醋搅匀,灌进“食母生”瓶子,这“再加工”的咸菜就成了美味佳肴。两年高中,七百多天,那口瓮里的咸菜竟让我吃了个净光光。临了,因为淹咸菜用得是粗盐,那瓮底经年积存了厚厚的一层黑泥,最早淹上的“辣疙瘩”、胡萝卜、白萝卜有些就埋在那层黑泥中。用手抠出来,可劲地搓、洗、涮、泡,经了“再加工”依然味美。那时,二姐已顶替父亲服工当了工人,第一回吃过二姐带回家的“榨菜”,想不到人间会有这么好吃的咸菜,就说于二姐:给卖点榨菜带学校里吃呗,二姐说:哎哟,多贵呀。
大姐夫姓牛,也养过牛,现在还养着一群羊。说:某人梦见“猪拱栏门”,释梦人讲:嗯,有人给你送吃的来。果然;又一日,某人梦见“猪拱栏门”,释梦人讲:嗯,有人给你送衣裳来。果然;再一日,某人梦见“猪拱栏门”,释梦人讲:有吃有穿的了还“拱栏门”,嗯,你这是要挨打。亦果然。这笑谈里的故事,我以为说的是要好生待成家里养的那头猪,因为肥头大耳的猪确是“大财”。所以到了快过年,在猪圈的栏门框往往贴上“六畜兴旺”的对子,所以照应猪的日常就有一口专用的“泔水瓮”。
“泔水瓮”置于猪圈门口的一侧,夏秋里浸泡的多是“打猪草”从田地间弄来的、经过剁切的各色野菜、秧叶和嫩草,冬春时则浸泡经过粉碎的豆秸秧、地瓜秧、干草秧和谷糠,这般经了浸泡和发酵,喂养的猪吃进肚子里消化得更快更好、“长膘”就更肥,待出了栏更能卖个好价钱。从生产队分到的地瓜中拣选出的“伤镢”、“小猫屎”以及涮锅洗碗水,也是便宜了猪们,毕竟人吃的东西总比“泔水瓮”里的高级得多呢。
“打猪草”“剁猪草”充实“泔水瓮”,基本属于家里孩子们去做的事儿。“打猪草”的孩子很少一个人独自到坡野里去,大都约上一帮子,一则更好玩、热闹,二来有照应、安全,有时得了机会还可站岗放哨偷个仨瓜俩枣。特别是秋天,玉米刚刚窜了顶缨,高粱适才鼓了苞穗,地瓜秧满满盖住了生长自己的黄土地,乎啦啦地一帮挎了筐子、拿了镰刀,蹦跳着“上了坡”。爬满地头堰边的“拉巴蔓”,不要;亦然蔓生、多得是的“窝揽秧”,不要;长势极好、鲜嫩的“地瓜秧”,不敢要,于是专挑了诸如青青菜、曲曲菜、蚂蚱菜、蓑衣草;大苦菜、小苦菜、大匐苗、小匐苗,还有唤作“老牛斜斜”的什么菜,几薅一把地装进筐子里。往筐里装“猪草”有门道,若是偷懒,胡乱地往筐里塞,尤其平口之后,用不了几把也就“满”了筐;如果下力,待平口后要依筐子的四沿,一把把、有序次、稳当当地摆放,如此这般就能渐次置顶筐系子,最后的几把还得用力塞摁进去,结实实一筐“猪草”看上去像一只绿色的花篮。打回来的“猪草”一定要剁碎了,不然就没法入“泔水瓮”、就不能够快地发酵,只是这地上垫块木板、手起刀落的一个人“剁猪草”实在不甚好玩,根本比不上约了一帮子的转转悠悠“打猪草”,更不用说还能摘到“天星星、酸溜溜、车厘子、托盘儿、大酸枣”或是玉米地、高粱地、地瓜地不小心长成的“甜瓜、懒瓜、小西瓜”这等可人的野味。只是一直弄不明白,当年“剁猪草”常见追花逐香的蜜蜂、蚂蜂、蝴蝶,会飞上那馊臭味的“泔水瓮”,还小心翼翼顺了瓮沿内壁往里爬,直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晓得一二。比如蜜蜂中的公蜂,其任务有着清晰的分工,细至“哺育蜂、采粉蜂、采水蜂、酿蜜蜂”,“采水蜂”就负责巢内蜜蜂饮水和巢穴湿度。如是,采水而已,无论何味。所以,蜜蜂也好,蚂蜂、蝴蝶也好,还会飞进猪圈、飞进鸡窝、飞上牛槽、飞进厕所,只要内里存在它需要和必得的东西。
“水瓮”这家什属大个头,夏秋放在天井,便于担水蓄水,可映日月;冬春大都挪到住屋正堂,防止冰冻挤裂,能鉴灯火。那从水瓮里舀水的什物,无论“轻铁皮”制的、葫芦瓢锯的,统称“水瓢”。四季里满村满胡同疯窜的孩子,玩累了、热坏了、口渴了,跑回家抓了“水瓢”舀起来“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凉水,也不拉稀。在平日,那水瓮就似母亲的专用,灌暖瓶、做粥汤、馏干粮、炒炖菜、泡煎饼糊糊,哪样都少不了摸索这水瓮。这么着,饭屋的灶台、住屋的炉台和一溜瓮沿,往往就是母亲从天明到熄灯的活动区域。“都是说呢,在家办饭‘睁眼到黑天’,忙活着哪”,不只一次听母亲讲过这话。
故乡水的来历廉价又金贵,哺育的躯体结实不矫情,滋润的灵魂韧性而柔软。每每记起盛下故乡水的水瓮、记起那些简洁明了的日子,感念恩情,不敢背叛。
 那时,村子里还没有通达地下水脉的机井,尤其入了冬,往往就闹水荒。想来天穹直下的雨水、房脊流下的屋檐水、从“羊沟”注入的池水、临水库凿坑的过滤水、磨盘顶融化的雪水,一应嘬饮过。有一年,自入冬到开春,水荒闹得紧,野坡里一口口的池子干了底,家中后院池子里的存水一次打不上半桶,那“水瓢”也就刮到了瓮底。这时候,同了比我大三岁的哥哥,用手推车捆上两只圆柱型的水箱,去五里外水库边的“滤水池”打水推水。把车子稳放好,“灌口”置于水箱的汲水口,我负责扶好了车子不至“偏沉”倾斜歪倒,哥则一桶桶从那“滤水池”提水再灌进水箱里去。看看水箱里的水已是漫到汲水口,哥就抬起车把并呼我提大半桶水再往水箱里灌。这是因为,平放地上的车子总令那水箱多少有些前高后低,并不“水平”,当了车把一抬,漫到水箱汲水口那儿的水就得了“水平”,这般看上去水箱还不算满,总能再灌进大半桶的水,如此推动起来的感觉才不致因了水在箱内的扰动而难驾驭。把两箱的水推到家,车子放稳了便要“卸水”。扶好车子和一只水箱,把另一只水箱朝上的汲水口拧转至外侧,接好水桶取了水再倒入住屋正堂那口水瓮里。最好是两只水箱交替着来取水,不然车子“偏沉”得厉害就不好扶,这样反反复复地,直到可以抬了水箱将所剩无几往水瓮空个干净。
那时,村子里还没有通达地下水脉的机井,尤其入了冬,往往就闹水荒。想来天穹直下的雨水、房脊流下的屋檐水、从“羊沟”注入的池水、临水库凿坑的过滤水、磨盘顶融化的雪水,一应嘬饮过。有一年,自入冬到开春,水荒闹得紧,野坡里一口口的池子干了底,家中后院池子里的存水一次打不上半桶,那“水瓢”也就刮到了瓮底。这时候,同了比我大三岁的哥哥,用手推车捆上两只圆柱型的水箱,去五里外水库边的“滤水池”打水推水。把车子稳放好,“灌口”置于水箱的汲水口,我负责扶好了车子不至“偏沉”倾斜歪倒,哥则一桶桶从那“滤水池”提水再灌进水箱里去。看看水箱里的水已是漫到汲水口,哥就抬起车把并呼我提大半桶水再往水箱里灌。这是因为,平放地上的车子总令那水箱多少有些前高后低,并不“水平”,当了车把一抬,漫到水箱汲水口那儿的水就得了“水平”,这般看上去水箱还不算满,总能再灌进大半桶的水,如此推动起来的感觉才不致因了水在箱内的扰动而难驾驭。把两箱的水推到家,车子放稳了便要“卸水”。扶好车子和一只水箱,把另一只水箱朝上的汲水口拧转至外侧,接好水桶取了水再倒入住屋正堂那口水瓮里。最好是两只水箱交替着来取水,不然车子“偏沉”得厉害就不好扶,这样反反复复地,直到可以抬了水箱将所剩无几往水瓮空个干净。
好在那年月的冬季和早春,老天爷并不吝啬,时不时自东南西北织来下雪的天,往往一场接了一场,只是总比不了夏日的雨水那么赶趟救急,更不会自己满满地落到家园和野外的池子里去。但是,逢了这天气,便可以不去也没法四下里打捞人蓄须臾不可或缺的用水。看看天井、胡同里的雪已是积了厚厚的一层、又积了厚厚的一层,一遍遍拿扫帚扫成堆或是归到墙根,待到雪停,即可“化雪成水”。就是把天井、胡同里的雪,千方百计尽多地填到后院那水池里去,以至填满了池子又在池口蓬了个雪盖子。更加有意思、有干头、有玩头的,属“磨顶融雪”了,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大致写过这场景。听了娘的吩咐,和哥哥一同拿了扁担、绳子、铁锨和“簸箩”,村外寻一处厚实干净的雪地,用铁锨由上而下铲切成四方形的块块,千万别刮了泥土,尽量齐底把切好的雪块铲进“簸箩”里,已是满满的了便撑绳子、顺扁担将一“簸箩”雪块抬回家。接下来的营生,就是把那雪块堆到推煎饼的磨顶上,把水桶接在“磨盘嘴”的下方,只待日头渐渐将雪块融成了雪水,装进那口水瓮里去。在我如今的感觉里,“磨顶融雪”一如“高山流水”,那雪块融化的就是清冽、就是爽甜、就是美好;那口水瓮一如故乡之眼,无时不在注视我的身影,亦无时不在透视我的心魂。
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坯一石,件件什物、幕幕景像,真如刻印在脑海里、存储在骨子里,无论走到哪,只要提及起来,便若石投水,涟漪环生。前几天,偶与同事谈到“三口瓮”,慨然认同那就是村庄曾经的、简洁明了的日子。村庄的日子晃晃悠悠走到今天,虽则“三口瓮”早已不是“标配”,却成了印记里无论如何都抹不去的底色。